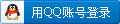一时兴起去剪了短发,短到洗头发的时候手里一点都抓不住。给我理发的是个个子不高有点微胖的男生,嘴巴有点大,抿嘴的时候像极了以前的一个同学,想不起来是谁,却也不反感。出了理发店回学校,越发觉得脖子细长,空荡荡的与风对峙着。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戏谑的对她们说:自从我剪了短发,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像个男的,我唯一不觉得自己像个男的的时候是我觉得自己像个妇女的时候。她们一边哈哈笑着说这句话好经典哦,一边得意地甩甩自己的长发,之后再安慰我说不是还有艳辉做伴呢嘛。进到教室,前排女生吃惊的看着我,一副没认出来的样子,说剪头发了?真下得了狠心!红红在一旁帮腔道,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我一本正经的说这是要洗心革面从“头”做人了。后排的胖子说:哥,大冬天的怎么把头发剪短了呀。不过还是心不够狠,要剪就剪成我这样的。说着,摸了摸自己直刷刷向上生长的三厘米的寸发。我表现出很欣喜的样子说好啊,下次理发一定要记得叫上我。这时,他身边的瘦子正咧着嘴笑,黑黑的皮肤衬的一口牙分外洁白。视线上移到他的头发,多么像是十月份的麦田:乍一看好似一片荒芜,隐约中又有些细瘦的麦苗正在顽强地发芽。我目测着,这是两毫米?不对,哪有那么短!嗯,是三毫米!心里快速确定了一个答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习惯短发,虽不漂亮不妩媚不俏丽不淑女,倒也干净利落。
寝室增添了一个大一的新生,我还记得她进门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来的好早呀。我说是啊,我们两年前就来了。小姑娘长得又高又瘦亭亭玉立的,整天嘴角挂满微笑声声学姐的甜甜叫着,每天零食不断却又不长胖,让立了三年减肥志的红红在一旁羡慕嫉妒地感叹,这少吃两年饭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我们七个土老冒静静的看着这位后生穿黑丝袜,百褶裙,纯白的斗篷衫,和她的小闺蜜们聊彩妆,盘发。面面相觑,由衷感叹后生可畏呀!我们都老了。。。
宿舍楼后面就是我们经常上课的教学楼,虽然简陋,却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位子,仅因为它有着观看窗外风景最美的视角。平坦的土地上零星点缀着几栋房屋,白墙红瓦。一畦畦规则的菜地由于品种和生长期的不同呈现出不同深浅的绿色,参差不齐但错落有致。前面则是一片杨树林,在初寒的冬天里呈现出红黄绿不同的颜色,像是一幅色彩浓郁鲜明的油画,那么丰富那么美不胜收。不知从何时起,不再那么喜欢淡雅素净,那张鹅黄中微带浅绿的hello kitty的床单不再像以前那么让我喜爱了,那些纯白色或碎花的衣衫被压在了衣柜的最底层。开始用明丽而浓重的色调布置和装扮周围的环境,越浓重越好。开始喜欢把自己隐藏在纯粹而深重的衣服里面,以前那些彩色条纹的衣服轻易不拿出来穿,嫌经常撞衫,也嫌花哨。开始觉得只有简单平凡的东西才能长久,就像之前,无论用什么发饰扎头发都觉得俗,所以一直只用一根黑色皮筋;无论戴什么饰品都觉得不够别致美观,所以一直什么首饰都不戴。我开始明白简单到极致原来也是一种不简单的长久。
倩姐终于和她的军人家属团聚了。时隔两年,那种强烈的思念与爱恋已被时光打磨的平静而圆润,静静的躺在心底不作任何表情的流露。冬日的早晨,五点多钟,没有曙光,没有晨曦,甚至没有东方微露的鱼肚白,在整个校园都还一片寂静的时候,我听见她麻利而果断的起床去接站,她其实一夜未眠。真正深刻的爱恋,不是相见时热切的亲吻或紧紧的拥抱,而是相视一笑,指着来时乘坐的出租车说,我们还坐这辆车回去吧。再见到他时,整个人瘦削也挺拔了许多,两年的军旅生活使他显现出了成熟与康健。饭桌上,倩在他身旁,露出羞赧而幸福的微笑,宁静而美好。我说倩姐你今天特别漂亮,她不好意思的脸红了一下。我转而调侃的问他,你觉得呢?他充满爱意和从容的说,我觉得一直都特别漂亮。众人皆开心的笑着。这时,窗外下起了雪,夹杂着小冰晶,轻轻敲打在被暖气附着着稍显白雾的玻璃上,即刻便融化掉。我看着这场景,想起朋友说的:这就是雨雪菲菲呀。我回过头来,看见桌上的小酒精炉里微弱的火苗摇摆着,锅里的白菜和肉块轻微的由中间向四周翻腾,热气袅袅的像炊烟一样向上渐渐弥散开来。每个人心中都充满温情。
与此同时,在我们温暖的小窝里,那盆台湾竹正苍翠的绿着,一如两年前相同位置上那束怒放的康乃馨......
我抬头望望窗外,似乎下的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