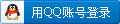淇河的沿岸建成了海滨似的沙滩,没有海的风情和漾动的波浪,也没有细软的海沙。只有停不下的车,挤不动的人,光着脚走在粗砾的河沙沙滩上,时不时被石头咯住脚,完全没了来之前的期盼和兴致。旁边的观景大厦还在施工初期,周围多了好多叫不上名的宏伟建筑,据说都是上海市的地标建筑。本来清澈的河水在众人的扑腾下成了母亲河水,我曾经堵车半小时带着泳衣和浮力袖来戏耍,却再不提下一次了。这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闭着眼骑车都不会撞到人的上海新区了,城市需要发展,但当我看到几乎所有的麦田都被楼房替代的繁荣景象,还是觉得没有了归属。那个我生活了10年的被朋友称为大观园的庄园,据说现在也是钢筋水泥和商业,自从那片土地上附着了水泥,我就再也没有忍心去看过。
我于是捡起了扔掉多年的毛笔,那套工具是我去年年末在师大拍卖会上以高出底价一元钱的高价拍回来的。幼时初写软笔的情景逐一浮现,时隔这么多年,依旧是那样的稚嫩水准。楼下适时的开了家书画店,名叫耕耘坊。坊主是位退休的爱好文墨的瘦削老头,这年头,凡是与文化沾边的店铺,其生意都不如路边的内黄灌肠,炸串和串串香。只见店外每天按时摆上各种字体的字画,却依旧清静无人。于是我总是多走几步路来学习和讨教一些,在我看来,人到了这个年纪,尤其是文化人,有了几十年的思想积淀和那个年代的专属经历,绝对算得上是智慧老人。坊主是河北人,曾在林彪的571部队参军,主修土木工程,这只是业余爱好,喜欢装裱字画和纂刻。店内悬挂的诸多字画都出自他朋友之手,像我这种基础水平,纂书草书基本认不得,能认得的字画中,自认为写的好看的是他的一个和尚朋友写的,他说这个朋友是真和尚,一辈子没结婚,现在也六十多了还在某山上。我想有机会到了某山上一定得拜访下这个和尚,说不定是个得道高僧呢,我也去接受下禅和知识的洗礼。练了一个多月的字吧,有些小进步但没有实质性突破,嫂子一语道破天机:我觉得和你的硬笔字写的有些像,不像书法。唉,我看我是成不了得道高人了,以后还要坚持写,丑也怡情。
好久没有写过东西了,也离文学很远了,有天晚上练字练的是宋词,才发现我竟然连李清照的声声慢都记不清晰了,啊。。。
秋天不多怠慢的走到了眼前,新生从凌晨开始就逐渐报到了。走在依旧干净的校园里,才突然发现这个被我妈戏称为半拉大学的大学生活也快要结束了,已然成为最老的一茬人了,从此步入大四,成为所有孩子们的学姐。我一向喜欢秋天,喜欢秋天的天高气爽、晚霞绚丽,多姿多彩,甚至它的清冷都是极好的。却在这样一个时刻,看着有七八层楼高的笔直的白杨在秋风中摇曳着,密密匝匝的树叶摩擦着沙沙作响,宿舍楼下那排初夏总是滴油被我们烦透了的栾树现在红黄绿交相辉映,茂盛而炫目的不可一世,那是傲慢吗?可为什么它们分明是那么美丽?学院的教学楼都被卖了,几乎所有的辅导员也都变更了。我才感觉到,原来秋天真的有种味道叫作凄凉。
那么多的同学,有的准备出国,有的在准备考研,有的准备就业。可无论那种选择,等到将来离开了大学校园,还是会怀念,还是会有遗憾,就那么深深的镌刻在不能更改的记忆里。有那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做,真的就时光不等人了?有没有一种职业叫作上大学?最好是带薪的。
有人说,人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循规蹈矩的活了20多年,敢恨不敢爱,敢说不敢走。我对寝室的姐妹们说,咱先从第二次冲动做起吧?她们笑着答应。在最后的一年时光里,好好看书,好好旅行,好好吃饭,好好纪念。青春本就很短,大学更短,有些事,再晚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