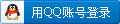他依据诱导分化学说,在大量实验基础上,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国际血液学界将其治疗方案称为“上海方案”。
■他在声誉达到顶峰时毅然“让位”,扶持年轻人走上科研一线。他愿做识途老马,让后人在艰辛的医学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恬淡清雅,也不失牡丹的王者本色!”
舞台上,演员话音刚落,一朵淡雅的牡丹在银幕背景上傲然绽放。观者无不动容。
近日,上海首场校园原创“大师剧”《清贫的牡丹》在上海交通大学菁菁堂上演,引发学子热捧。“牡丹”的原型人物,正是我国血液学专家王振义院士。
从医六十多年,王振义硕果累累。他的最大成就,是改变了用化疗杀死所有细胞的传统疗法,而是用诱导分化的方式使癌细胞“改邪归正”,成为正常细胞,让一个个白血病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1994年,王振义获得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评委会称他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2011年,已87岁高龄的王振义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振义收获鲜花掌声无数,却最爱一幅国画《清贫的牡丹》。牡丹出身富贵却甘于清贫,正合他意。
当年在震旦医学院求学时,王振义立下医学誓言:余于病患,当悉心诊治,不因贫富而歧视,要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造福人类。
一个多甲子过去,王振义从不曾忘。
找到一把神奇的“钥匙”
1985年,在上海儿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死神正对5岁的小女孩严怡君虎视眈眈。严怡君高烧不退,口鼻流血,内脏器官多处感染。医生已经束手无策,小女孩眼看撑不过几天了。
她患的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白血病本身就已经是“血癌”,是绝症,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白血病中最凶险的一种,发病急骤,病程短促,死亡快。快到什么程度?从送进医院到死亡,往往不超过一个星期,甚至只有两三天,绝不给医生留一点点机会。
化疗后的女孩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死神已扼住了她的喉咙,守在床边的母亲眼泪都已经流干……
女孩在上海儿童医院医治,王振义的夫人谢竞雄是儿童医院的儿科血液病科医学顾问。妻子从病房带回来的信息使王振义彻夜难眠,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给病孩口服全反式维甲酸。
全反式维甲酸原本是用来治皮肤病的,但王振义团队在多年实验中发现,大量急性早幼粒细胞在这种药物的作用下,奇迹般地“改邪归正”,变成了正常发育的细胞。王振义提出,既然已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为何不让她试一试这种药?
妻子疑虑重重:“你们的实验是在体外做的,进入人体后究竟会怎样?假如不起作用病人死了,我们能说得清吗?”
王振义沉吟片刻:“这我也想到了。可凡事总有第一次,第一次总会有风险,对吧?”
“这可不是一般的风险,是人命啊!”
“正因为是人命,就更有必要、更值得去冒这个险了。假如成功,可以挽救多少人命?”
妻子深深地叹着气:“我何尝不想救人命。可要不成功呢?麻烦就大了!你能保证成功?”
王振义默然了。的确,他无法保证成功。
类似的讨论也在王振义的课题组进行。每次讨论,都转了个圈又回到原点。
这天,妻子告诉丈夫:小怡君已气若游丝,每一分钟都面临死亡。
寂静中,王振义直视着妻子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竞雄,你我都是医生,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对吧?救人一命是天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谢竞雄读懂了丈夫眼神里的决心,含着泪用力点头。
王振义说:“我想好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把双手用力按在妻子颤抖的肩膀上。
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小怡君接受了新的治疗。服药几天后,小怡君病情没有继续恶化;一个星期后,原本已烧得神志不清的她睁开了眼睛;一个月后,病情完全缓解……29年后的今天,小怡君依然健康地生活着!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例口服全反式维甲酸而成功治愈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人。
当时,看到疗效后,王振义极为振奋。他安排学生骑着自行车到全市一家家医院去寻找,找什么?找病人!每找到一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人,他就力主推进试用新疗法。就这样,一年时间里,王振义又陆续治疗了24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病人,病情缓解率超过了90%。
王振义的一位部下忆起当年,至今心有余悸:“想想,这24个人,虽说个个已被‘宣判死刑’,但其中只要有一个出了问题,试验就有可能被中断,前功尽弃。王老师那会儿已经是名医、教授、校长,弄不好名声也完了,前途也没了。多少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王振义何尝不知其中风险?但他心里太明白了:从1个成功病例到24个成功病例,这意味着他们已在凶险莫测的白血病领域里,大海捞针般找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正在神奇地打开一把人类医学史上从未开启过的“锁”——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这说明了什么?
此前,在与此种恶疾的残酷抗争中,人类败绩累累,但从此刻起,历史要改写了。一个历史时刻正在降临!
名师高徒携手闯关
顾不上庆功,顾不上申报奖项,更顾不上申请专利——在临床已经证明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神奇效果后,王振义马不停蹄地着手做第二件事:推广,抢救更多已命悬一线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为了尽快推广新疗法,王振义团队从1987年起开始撰写论文。“但在向国际著名血液学期刊投稿时,论文两次被质疑。第一次说结果令人怀疑,学术上有问题,第二次说英文写作有问题。当时,一位著名的美国血液学教授正在上海访问,他看了研究结果后觉得很不公正,于是按美国人的英文标准将论文重写了一遍,并要求该期刊务必接受,这样论文才得以发表。论文发表后即引起轰动,被誉为白血病治疗的‘中国革命’。”——这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给中科院研究生讲述的一段故事。
陈竺所说的期刊就是美国的《Blood》(《血液》)。当笔者向王振义求证这段故事时,王振义脸上漾起了微笑:“这很正常嘛!在他们心目中,当时中国的医学至少比发达国家落后了20—30年。他们怀疑我们在造假。好在还有法国人、美国人与日本人也在做嘛,一调查,说是真的,论文就发表了,那是1988年。看来还是沾了这些外国人的光喽!”
就是这篇曾被怀疑造假的论文,截至2010年,已经被引证了1700多次,并获美国ISI引文经典奖。2000年,一些著名美国教授编了一本有1000多页的书《20世纪具有标志性的血液学论文》,收集了世界各国的86篇论文,此论文也名列其中。
在医学界,临床药物的成功,只是成功了一半。从分子与基因的高度,弄清致病机理,以及药物如何在人体中起作用,才是征服恶疾的最高层次挑战。
1989年7月,陈竺、陈赛娟夫妇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来到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在这里迎接他们的,正是当年把他们派出国的导师、血液研究所所长王振义。为让研究工作迅速展开,王振义已为他们申请到两万美元霍英东科研基金,作为科研启动经费。
在陈竺出国前,师生俩多次促膝长谈:中国的血液病学科如何发展?如何创新?“经过‘文革’,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了,派你们年轻人出去,就是为了把国外先进的科技学到手,拿回来。我们老了,学科的发展今后就靠你们了!”王振义对学生寄予厚望。
研究小组对白血病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在研究所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起步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骑辆自行车带着瓶瓶罐罐到外边借实验室做实验,成了陈竺每日的“功课”。而王振义则开始了真正的“七十学艺”:戴着老花镜向自己昔日的学生刻苦学习分子生物学的相关课程。陈赛娟呢?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老师王振义主要从事白血病的临床治疗工作,陈竺主要进行分子细胞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怎样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成了我的研究重点。我成了老师和陈竺之间的桥梁,用陈竺的研究成果,确定白血病病人的分类、分型,在老师临床治疗不同病人时,给他提供一种适宜的治疗方案。”
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日后,这3个同门师生竟个个成了院士,成了身怀绝技、名扬国际医学界的医学大师。
1990年,研究小组找到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特殊基因改变,从分子学的高度揭示了该疾病的发病机理;同年,研究小组又发现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特殊亚种”——此类患者对全反式维甲酸毫无反应。跟踪观察了一年多,发现这是因为11号染色体与17号染色体发生交叉,形成一个新的融合基因,导致癌细胞产生了耐药性。
一种是耐药的特殊亚型,一种是对全反式维甲酸敏感的经典类型,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与区别?经反复比较研究,全反式维甲酸对早幼粒白血病诱导分化的机制,终于真相大白。
现在,美国、法国等国的同行们遇到“特殊亚种”病例,都要专程送到中国,请上海血液学研究所鉴定后才作定论了。
主动“让位”提携后辈
1994年初春,一封邀请函寄到了王振义的办公室。王振义一看,愣住了:自己已被授予凯特林癌症医学奖,与法国的同行劳伦·德古斯共享。主办方邀请他亲往领奖,并作关于“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学术报告。
凯特林癌症医学奖由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设立,用于奖励对癌症治疗与研究做出创造性杰出贡献的医学专家,被公认为肿瘤研究的“诺贝尔奖”。
领奖地点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厅。1994年6月15日,几百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癌症医学专家聚集一堂,第一次有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登上这个领奖台。
这一年,王振义70岁。随后几年间,他收获了众多荣誉: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7年获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1998年获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2003年获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
声誉如日中天之际,他却认定,自己需要“让位”了。
瑞金医院接到王振义的辞职报告十分为难。不错,他的学生们是非常优秀,但从某种意义上,上海血研所代表着中国血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所长这个位置,王振义是当之无愧的。他刚在国际上荣获凯特林大奖,又当选院士,现在易帅合适吗?是的,他年纪大了,但他身体不错呀,还一直在临床与科研的一线,又有什么必要“让位”呢?
但王振义找到院长,讲了他的“抛物线理论”。他说,人生就像抛物线,人的体力、创造力达到某个高度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下降趋势——这是自然规律。“我主张,在有能力时要努力地干,一旦进入‘下降通道’了,就要有自知之明,及早地退,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干。”王振义说,“因此,请你们尊重我的意愿。我最乐意看到的,是血研所能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至于我个人,退下来后也不会闲着,我会当好顾问,当好士兵。”
王振义坚请“让位”的事,让陈竺、陈赛娟终身难忘。
是王振义,在1978年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陈竺这个“中专生”做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他又手把手地指导各项实验,把他们一步步领入了神秘莫测的血液世界,后来又一起撰写系列论文。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王振义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习以为常的中国学术界来说,真乃破冰之举。
“文革”打断了一代人的职称评定。到1981年,已58岁的王振义还只是个副教授,他需要评教授,所以非常需要有自己署名的论著,但他还是把学生推到了前面。
如今,陈竺夫妇早已双双成了院士,陈竺还担任过7年的共和国卫生部部长,陈赛娟也早已接过了上海血研所所长的担子。她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仅30岁的科研队伍,承担了17项国家重点项目与国际合作项目,每一项都瞄准了领域前沿。
更令王振义感到欣慰的是,所里的良好学术氛围代代相传:近年来,全所在国内外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69篇,年轻人为第一作者的达67%;每周一次文献报告会,由研究生轮流主持;每两周一次数据分析会,各研究小组将自己发现的数据拿出来供大家分析,在这样的学术会上,人人平等,为了一个问题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也许早在“让位”之时,王振义就已经预见了这一切?

王振义在自家客厅,墙上画作为《清贫的牡丹》。
耄耋之年学无止境
王振义早年毕业于震旦大学,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但英语却是他的弱项。为了与国际上更多的血液学专家交流,他开始学习英语。当时,他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了。
王振义的孙女王蔚记得,自己每次去爷爷家,都可以看到他的单词笔记本里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二十多年的坚持,让他在耄耋之年能够说出和法语一样流利的英文。
王振义永无止境的学习劲头,还表现在他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上。平时,学生们总能看见他在闲暇时学习幻灯片的制作,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安装软件和国外的亲朋好友视频通话。他特别有好奇心,每次发现有什么好用的软件,都会兴奋地学习操作,就像一个永远抱有新鲜感的“孩子”。
王振义说过,他退下来后也不会闲着。那他究竟还想干些什么呢?他不愿意写书,他说:“写书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不想写。现在医学科技发展太快了,等我忙乎两年,写出一本书来,内容已陈旧了。”
如何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余热”?最终,他想出了“开卷考试”——不是他考年轻人,而是让年轻人考他。每周,瑞金医院血液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会把临床上无法解决的难题出给王振义,让他来解答。王振义一般用3天的时间准备:先了解病人情况,再查阅国内外最新资料,然后做成多媒体课程。每到“答题”这一天,20多平方米的血液科医生办公室里总是爆满,以至于后到者只能站在走廊上伸着脑袋看,伸长耳朵听。
对于“开卷考试”,王振义觉得好处很多:“首先是有利于病人,可及时解决临床上提出的疑难问题——我穿了一辈子白大褂,为病人解除病痛,是我最大的满足啊;第二,有利于年轻医生以最快的速度成长,他们现处在第一线,太忙了,没空从网上看那么多东西,而我退下来了有很多时间,可以搜索、阅读、下载本领域最前沿的东西,经过汇总、分类,直接提供给他们,谁要对该课题感兴趣,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嘛;第三嘛,呵呵……”每每说到此,这位老院士总会禁不住笑出眼泪,语调里有着不无得意的快乐:“这第三是对我自己有利呀,多动脑,多思索,可防止老年痴呆症嘛!”
他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诠释,唯有爱病人,一个医生才能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有了爱,我们才能不断督促自己学习,充实自己,从中累积的经验才能成为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利剑。”他说,自己这匹识途的老马愿意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贡献给年轻人,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他还说,自己能做的事情不多,唯有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年轻的医生们一些启迪,让他们在艰辛的医学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2010年12月,就在王振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前夕,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王振义失落地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与这位他生命中最爱的人分享这份荣誉。
王蔚说:“奶奶的病让她忘记了我这个孙女儿是谁,也时常会记不得我的伯伯、爸爸和叔叔都叫什么,但她始终没有忘记的就是爷爷的名字。奶奶走了以后,爷爷每周都会买一束白色的玫瑰,摆在她的遗像前。”
很多年来,王振义和老伴过的都是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们傍晚常在一起散步。那时周围的路还在修,高低不平,王振义就紧紧地挽着谢竞雄的手臂,谢竞雄靠着王振义,深情地说:“现在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在王振义家客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国画,画的题词是“清贫的牡丹”。王振义曾这样解释:“牡丹嘛,大红大紫,一般都象征着荣华富贵,但我这幅牡丹却是白中带粉,很恬淡、清雅——我喜欢。但光是恬淡、清雅是不够的,人要有志向,要做一番事业,这又如牡丹的雍容大度。”
这幅画,不正是王振义人格的写照吗? (通讯员 樊云芳 倪黎冬)
《中国教育报》2014年12月5日第5版